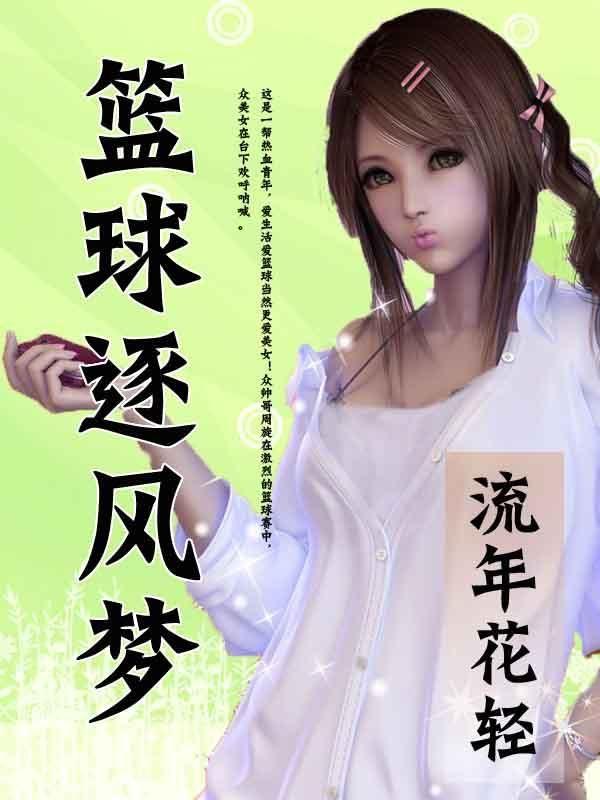青豆小说>凤舞朱阑 > 第322章 北狄合作龙脉共守(第1页)
第322章 北狄合作龙脉共守(第1页)
清晨的阳光洒在宫墙上,落在凌惊鸿的手背上。她站在东阁外的石阶前,指尖还残留着一点血迹。北风拂面,夹杂着铁锈的气息,让她想起昨夜天牢中苏婉柔那句低语——“你是在送葬”。
她没有回寝宫,也未召人议事,只是静静地站着,仿佛在等一个人。
脚步声由远及近,是皮靴踏在青砖上的声响。沉重而有力,与禁军的步伐截然不同。
巴图鲁来了。
他披着狼皮大氅,腰间悬刀,脸上带着酒后的红晕,眼神却格外清亮。站定后,他抱拳行礼,声音粗哑:“昨夜我做了个梦,梦见龙脉断了。”
凌惊鸿未动分毫。
“不是寻常的梦。”巴图鲁凝视着她,“我们族中的萨满用羊骨占卜,连烧三次,裂纹皆显示中原主龙脉将崩。若主脉毁,北地亦难安。山会塌,河倒流,牛羊尽亡。”
他顿了顿,语气沉沉:“祖训有言,龙脉非一家独守,北狄为辅。主脉一毁,我们同样难逃劫难。这不是你们的灾,是我们所有人的劫。”
凌惊鸿终于抬眼,直视巴图鲁。她闭目片刻,再睁眼时已运起望气术——这是她前世唯一记得的能力,无需念咒,只需凝神便可窥见气运流转。
刹那间,她看见巴图鲁头顶升起一道紫气,如烟袅袅,与地底某处的波动遥相呼应。更奇异的是,那紫气之中隐约盘踞着一条龙影,头角初现,鳞片未全,却透出一股凶戾之气。
北狄王族血脉,竟能与中原龙脉共鸣。
她收回目光,神色不动。
“你说合作,凭什么让我信?”
“凭这个。”巴图鲁解下腰间短刀,递上前,“北狄使者入中原,从不佩兵见君。但我今日带刀而来,便是不怕死。”
凌惊鸿并未伸手去接。
就在此时,又一阵脚步传来。
周玄夜到了。
他身着常服,未戴冠帽,手中捧着一只锦盒。面色苍白。他不知昨夜《血噬录》之事,却知凌惊鸿今日要说的话,不容第三人听闻。
近日宫中动荡不安,人人自危,仿佛大变将至。
他走到二人之间,先看了巴图鲁一眼,随即望向凌惊鸿:“你要我说什么?”
“说真话。”她直视他,“你相不相信,这世上有一扇门?一旦开启,百万人将死?”
周玄夜沉默数息,缓缓打开锦盒。
里面是一枚玉玺。
崭新,材质非金非玉,通体暗青。底部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昨夜内务司连夜所制,用的是前朝余料。”他低声说道,“传国玉玺失落数十年,如今归来。我不知它是否仍有神效,但我知道——若有人不信天命,便让他亲眼看看何为天命。”
凌惊鸿点头。
三人立于东阁之外,阳光洒落,映出三道身影。无盟书,无仪式,唯有三双眼睛彼此对视。
“我守北线。”巴图鲁道。
“我持玺镇宫。”周玄夜答。
“我查幕后。”凌惊鸿接。
话毕,三人同时抬手,掌心相对,未触即收。
就在此刻,角落寒光一闪。
一名“禁军”从柱后暴起,剑锋直刺周玄夜后背。出手迅疾,角度狠辣,分明是杀手无疑。
但巴图鲁更快。
他未回头,身形已侧,反手拔刀横斩。
“咔!”
刀过之处,血花迸溅。
那人右臂齐肩断落,长剑脱手飞出,撞上石阶,火星四溅。断手仍在抽搐,五指仍紧握剑柄。
全场骤然寂静。
凌惊鸿上前蹲下,掰开死士手指。剑格内侧刻着一个标记——三道螺旋盘绕成蛇形,尾端分叉如叉。
她瞳孔微缩。
这图案她在血池见过。青铜柱底便有相同刻痕。那是慕容斯家族的秘密家徽,外人绝不可能知晓。
她抬头看向周玄夜。
周玄夜也在凝视那把剑。忽然冷笑一声,高举玉玺,厉声道:“奉天承运,谁敢犯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