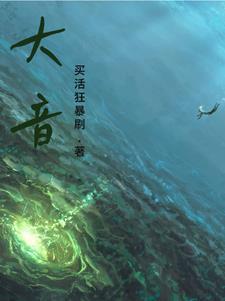青豆小说>画舫无风月 > 22第 22 章(第2页)
22第 22 章(第2页)
顾喟挡开花妈妈,对巧珍说:“怪我没有护好你。”
巧珍嘴上仍在客气,实际却用最美的仪态,把受伤的肩膀递上去,他把药油在鞭伤上一拖,巧珍“嘶”地倒吸一口气,娇滴滴喊了声“好痛”,却在顾喟停手时指点:“这药油要拿暖暖的手心揉开到肿了的肌肤下面去,才能起效。”
顾喟手顿了顿,瞥了瞥旁人,说:“伤得到处都是,要不,请其他人回避一下,我慢慢给你上药?”
花妈妈见养女又犯花痴,出声提醒道:“巧珍,顾大人是巡按钦差,你怎么当得起?”
顾喟冷冷瞥向她:“花妈妈,这话倒似不信任我?你要觉得我讨人厌,就直说罢,我也不缺一个花月舫的船娘伺候。”
花妈妈不敢得罪他,语塞片时,急忙千招呼万道歉的。
巧珍却心头暗喜,假意推辞了一声,见顾喟并不是要离开,于是反而向花妈妈眨眨眼,说:“妈妈,顾大人伺候奴,奴也要伺候他的。疼是疼的来,但擦了药就好多了。”
花妈妈见她不懂轻重,急也白急,苦笑一声告了退。
顾喟于是先把门关好落销,又把窗帘拉起。
昏昏灯下,巧珍眉目含春,抚着自己的胳膊,笑道:”顾大人,这间屋子是客人更衣用的,窄小简陋了点,你别嫌。“
不过窄小有窄小的趣味,给客人用的屋子也都是装饰精洁,更衣的矮榻铺陈着厚厚的锁子锦棉褥,上面摆着六个厚实引枕,一边是散发出“雪中春信”合香气息的熏笼,旁边还嵌着锃亮的铜镜——想什么姿势都行,还能瞧一眼自己个儿的“活春。宫”,别有韵致。
顾喟继续给她背上上药,好像有点敷衍,也没“拿暖暖的手心揉开到肌肤下面”,他在她背后,沉吟了一会儿说:“巧珍,我与你相处也有些日子了,你应当信我的人品。”
巧珍含羞道:“顾大人是真正的君子,奴奴当然信顾大人。”感觉他裹着手巾的手指已经在擦她腰上的鞭伤,于是装作疼痛扭了扭腰,又提示他:“其实……裙子里面伤得更重。不过,那种腌臜地方太污人眼了,那里可不需要顾大人上药……”正话反说,听得懂的急色儿郎自然要顺着这个借口好好饱览裙下风光。
但这位探花郎在这方面是个呆子,果然没听懂暗示,而且彻底停下手,压低声音说:“我来苏州这段辰光,很是厌恶刘知府,尤其他这样对你。不过这话你知我知,说出去对我不好,对你更不好,懂不懂?”
“……懂的。”
“他这样对你,我一定要弄个苦头给他吃吃,好歹我也是巡按御史,不能让这个贪恶的官员一直逍遥。而且,他若还仕途顺利,更可以在苏州说一不二,你将来日子可就真苦了。”
巧珍想到自己在刘北辰治下,确实被他看上了后面会苦楚无穷,不由害怕得落泪,转身拉住顾喟的手:“顾大人,你带奴奴走吧!奴奴是受不得了。”
顾喟裹着手巾的手抽出来按住她的手,沉重地摇摇头:“巧珍,我和你说实话,我正是怜惜你,才不得不斩断情丝。我娶的是首辅的孙女儿,她一向骄纵惯了,哪受得了我带妾回去?相府里折磨婢妾的手段更是你想象不出的,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主母打你、罚你、杀你,从狗洞里把你拖出去扔乱葬岗上,跟折一根草似的简单,也没人敢管,我只是七品小官,也不敢和岳家对抗。所以你说,我岂能把你带到那个火坑里去?”
巧珍听得心下惨然,真正痛哭起来。
顾喟拍拍她的手:“莫哭,莫哭,其实只要刘知府不缠着你,花月舫日子还是自由自在的,将来找个正常恩客嫁了,好日子也就来了。”
他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小锦盒,打开里面是个银镀金嵌宝的挑花头面,小心翼翼戴到巧珍的发髻上,含笑道:“真好看。你懂不懂我的心意?”
巧珍看他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眼睑上的淡粉色仿佛是心疼她而带出来的酸楚,她伏到顾喟怀里点头:“奴非草木,孰能无知?顾大人都是为奴好,奴奴这辈子有个知疼着热的人,也就心满意足了……”确实悲从中来,又哭了一场。
顾喟等她哭完,把手绢递过去,见她擦了泪平静了,于是说:“我位不如知府,虽然知道一些吴县赈灾和漕税的情弊,但要凭此弄倒刘北辰,只怕最后只是王县令背黑锅,而撼动不了其他人。所以,要是知道刘知府自己做了什么作奸犯科的事,让蒋巡抚无法保他,只能挥泪放弃,哪怕就是把这个畜生调任到其他地方避风头呢,也不会再来祸害你了,是不是?”
又悄悄说:“而且你放心,王知县已经是我的人了,只是他还畏惧知府淫威,必须得我叫他知道一切在我控制之中,他才敢反戈一击。”
巧珍点点头:“对的,刘知府别号就叫’缺德‘,说明大家都厌恶他,但他和蒋巡抚关系如穿一条裤子一般,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出首他的那些恶事。他确实是想害顾大人你呢,你这样一提醒,奴倒是想起了他们在知府后衙嘀嘀咕咕商量的是什么了。”
顾喟微微一笑:“他的名字应该出自’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以他字‘为政’,却没有‘以德’,号‘缺德’真是再贴切没有了。你说吧,听到了什么?我来想办法给你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