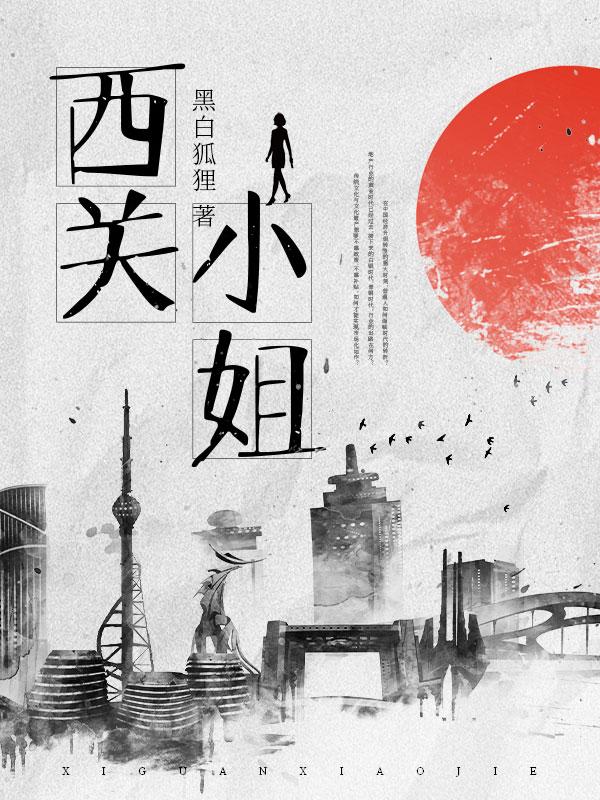青豆小说>东北糙汉捡到娇气包后 > 145150(第11页)
145150(第11页)
亲亲他的脚趾,或者让他这白皙的脚心落在自己的脸上。
这种事实在下作,听着就是流氓行径,像少爷这种出身的人,心中定会唾弃这种行为。
这位大当家从来也不是什么善男,如今在自己的地盘,心中所有的恶事都想要一一做个遍。
他就是匪,掳人上山,自然是要当夫人的。
早起他就想亲一亲人,但少爷昨天在马上累坏了,睡的很沉。
他便钻到被子里,本想把脸埋在这双玉儿一样的白腿中嗅一嗅。但真碰上了便忍不住想亲,饿的心发痒。
关少爷都是被他烦起来的。
阿东舍不得再弄他,便只能小心翼翼的亲,越小心,反而越痒,他实在受不了,被逗的直笑。
“还疼吗?”他轻轻将人圈进怀中问。
“嗯。”关少爷面颊微红,脖颈也是被吻的发烫,“疼呢,你掳我上山,如今真是半点都不疼我啦,阿东,你再这样,我便要厌你了!”
“别,别…”
少爷一说要厌弃自己,他可真是着急,拉着人的小手仔仔细细的在唇瓣边吻,“别厌我,少爷…”
两人的长腿交叠,在被子里缠绕着。
这两年阿东可从未舍得碰他半点,最多便是晨起睡醒嘴巴对嘴巴的喂水。
关少爷的身子骨太弱,昨儿在马背上那样弄,今儿实在起不来。
甚至身子还有要发烫的意思。
阿东便差遣人赶紧去隔壁县城找郎中。
其实关少爷这是娘胎里面带的病症,实在是没有办法根治,除了好好将养也没有别的法子。
阿东这两年已经找了不少郎中来看,都不行。
倒是听说西洋医会好些,只是凌县附近没有什么大城,真想要瞧西洋医,就得去南方,像上海那边有租界,倒是能找到医生。
如今世道这么乱,关少爷不想往外走。
他从小生长在凌县,自己的身子骨没有人能比他再清楚,只是昨天阿东弄的太狠了,马儿又颠簸才身子发烫。
“你以后就不能轻点?”他小声问,指尖就在阿东的脸颊上游走,“能不能对我好些?好阿东,不要那么对我…行不行?”
这位大当家曾经带着兄弟们出来闯天涯什么事情没见过。
如今真被绕指柔给缠住,软甜的声音入耳,魂儿便要跟着飞走,“好,好。”
关少爷瞧他这副呆样,又忍不住笑的肩膀直颤。
阿东的年岁要比关少爷还大上八九岁,见识的事也比他多,可偏在这种事上又大胆又笨拙,根本受不住半点撩拨的傻子。
阿东太喜欢少爷了。
想到当年他中枪时,少爷变卖项圈只为了给他治病。
他在重伤后醒来,第一眼瞧见的便是俯趴在床榻边熟睡的少爷,软白的小脸,令人难忘的震撼,粗粝的手指甚至不敢轻易去触碰他的脸颊,生怕自己的手会伤了他。
父母早亡,男人要顶天立地,作兄弟们的老大,引领着多少人在陌生的地方安家。
但这些年,只有醒来的少爷柔声细语的笑着问,“你醒啦?还疼不疼?受了好重的伤呢,瞧着都让人心惊…疼坏了吧?”
哪里是疼坏了,分明是心口软极了。
至于少爷的项圈,自然是给抄家拿了回来。
让那李老板拿去献给县官了。
在县官家里发现的,不过可算是找到了。
白玉的项圈重新戴在了少爷的身上。
在这土匪窝子里,个顶个的糙汉子,下雪天更是只能几层棉花袄子在身上套着防风。
但关少爷却穿着一身淡青色长衫,身上披着狐狸大氅,安安静静的坐在摇椅上翻书本,美人儿脖上再戴个项圈,玉衬的人更像妖。
屋子里的火烧的极旺,暖的不行。
凌县不少事情需要大当家的出面做定夺。
土地主得收拾,敛财好色的登徒子得处理,不少事,外面威风凛凛的大当家一回了寨子,赶紧朝着自己的院里走。
屋里头的人听见了声,赶紧起身掀开帘子,冒着雪出来接人。
大当家便直接半路将人搂进自己的斗篷里,听着怀里的人喊他,“阿东。”
“怎么出来了?”
关少爷脖颈上的玉项圈和他身上的金属扣子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