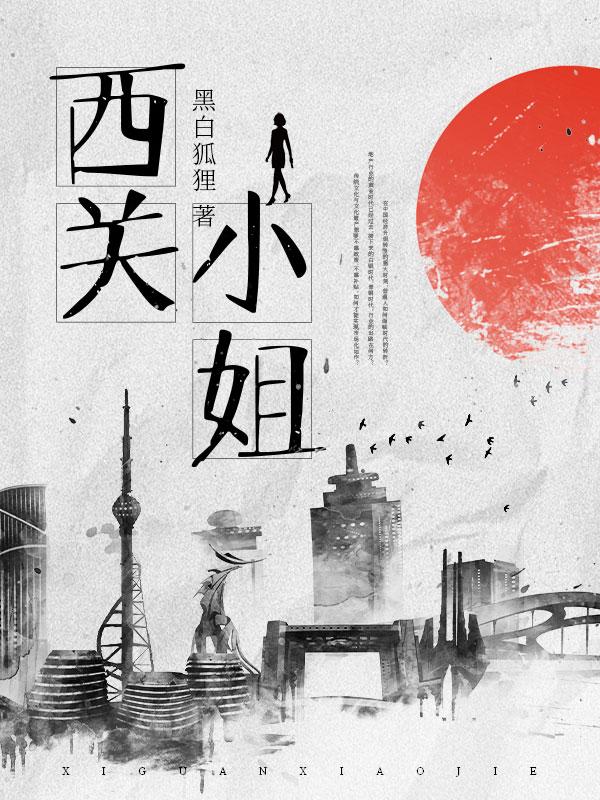青豆小说>东北糙汉捡到娇气包后 > 95100(第5页)
95100(第5页)
上面放着针。
得扎一下指腹看看他的凝血程度,采个样送去化验,等复查时候好出结果。
关灯一听要扎指腹有点怕疼,干脆脑袋往陈建东怀里一插假装听不见。
陈建东扶着他的手拜托护士轻一点。
只是拿针扎了针眼大的地方,关灯疼的倒吸一口气。
护士扎完以后不动的手,这个小针眼冒出了血珠后没停,血珠越来越大,最后快要掉时护士拿着试管接住,用棉签止血才停。
手术刚结束时吴医生说过关于凝血的问题。
关灯还不知道,但陈建东看出来了,正常人要是用针那么扎一下即便有血珠也应该只有一点点,不应该滴下来。
正好陶然然他们上外头买棉花糖回来了,陈建东放下饭碗,“哥去和吴医生聊两句。”
关灯就盯着陶然然手里的糖:“昂!”
陈建东从陶然然身边路过说:“就能给他一个,多了不能吃,平!盯着点,吃多了不行。”
关灯现在只能吃护心的菜谱,这些糖之类的东西是增加负担的,不能多吃。
“知道了东哥。”陶然然乐呵呵的进门,让他哥去帮着收拾行李。
他坐关灯病床旁边,俩男孩分吃自己的棉花糖。
陶然然悄悄说:“不觉得这个棉花糖大?”
关灯点点头:“大啊!比强子买的大好几圈呢。”
“我就知道东哥肯定不让你多吃。特意让大姨加了半勺糖!你多吃半勺能行吗?”
“哎呀我哥听风就是雨,没见过有人吃两块糖就心脏受不了的,吴阿姨说少吃,但没说不让吃,行啊然然,聪明多了!”
陶然然和他眨眨眼,俩人揪着蓬松到脑袋大的棉花糖一块块含在嘴里,他忽然想起来一件事,“你知道吗?钱猛腿断了。”
“啊?”关灯张大嘴巴,眼珠一转,悄悄问,“我哥干的吗?还是你哥干的?”
陶然然摇摇头:“他爹!听说被他爹打断的。”
关灯更震惊了,不过心里也畅快,要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吃这么多苦吗!他甚至在心里坏坏的想,如果是自己弄断的就更好了!肯定更爽。
“不过他爹为什么打他啊?”关灯好奇,“他不是家里的大少爷吗?竟然还能挨打呀?作弊被发现了?”
孙平耳朵灵,听见俩人在那研究,“我就在这呢。不问问啊?”
“平哥,你知道?”关灯愣愣的瞧他,还以为他开玩笑呢,笑着说,“你打的?你也生不出来这么大儿子吧?”
孙平:“…”
“钱家在北京卖建材的。”孙平说。
钱家是老北京人,听说这姓都是祖宗辈什么王爷亲王赐的。在老北京做生意很多年,全面经济开放后全国各地的厂子效益都不好,钱家三十多年前开始干建材。
近几年从南方进货在北京卖,长亮建材进北京以后抢走了至少大半的生意。
同行嫉妒的事很多,但有头脑的都会互利共赢,不少北京本地的建材公司知道长亮的价格低廉,也会从长亮进货。
钱家也是其中之一,放弃了南方的原料厂,从长亮拿水泥往外销。
目前长亮建材的基本销售还在东三省,最远也就到北京天津,南方还没涉及,他们就拿着长亮的货往外卖。
出了关灯这事后,陈建东就觉得那个姓钱的耳熟,一时半会没想起来,还是关灯做完手术后才清楚这小孩到底是谁家的。
陈建东直接断了钱家的货源,并且贷款一个亿砸中了钱家原本想要发展的地皮,直接从陶文笙那打的借条,等明年九良苑开盘再让三个点。
陈建东记仇这点特别邪乎,真踩了他命根子不往死里整他都不姓陈。
钱猛自认为自己是公子哥,以为关灯他哥就是给自己家搬水泥的工人,一惹下去家里都要破产了。
钱老板想破头都不知道究竟是哪惹了陈建东,这小子虽然到北京初出茅庐,却正经有点手腕,和当官的能吃上饭,和工人也能搬砖。而且就像是有预知能力一般,回回能在政策发出之前抢先行动,买地,招标,样样都是。
钱老板约了好几次陈建东没约出来。
最后一天是求着孙平要见见陈建东。
陈建东就让他带钱猛来,在关灯睡着后拿着尿壶出来倒的空隙下楼见了一面。
钱老板虽然是父亲,到底家里十几个亲戚都跟着自己做生意,真要被整倒了,他这辈子都完了。
他把儿子往前一扔,只要能消气怎么都行。
陈建东让孙平掏钱。
孙平钱包里现金不多,几百元,陈建东就问钱老板这些够不够买他儿子一条腿。
卖儿子一条腿能公司活命,今天陈建东不满意,货再停供下去,上千万的违约金他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关灯还在恢复期,陈建东没沾手这些事当积德。
钱老板自己动手的。
陈建东让他们换个医院治腿,转头就上了楼给关灯剪指甲。
孙平在病房里学:“你是没看到那场面!老带劲了!在医院车库他爹就那么揍儿子,然后都不敢带人上楼瞧,最后开车拉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