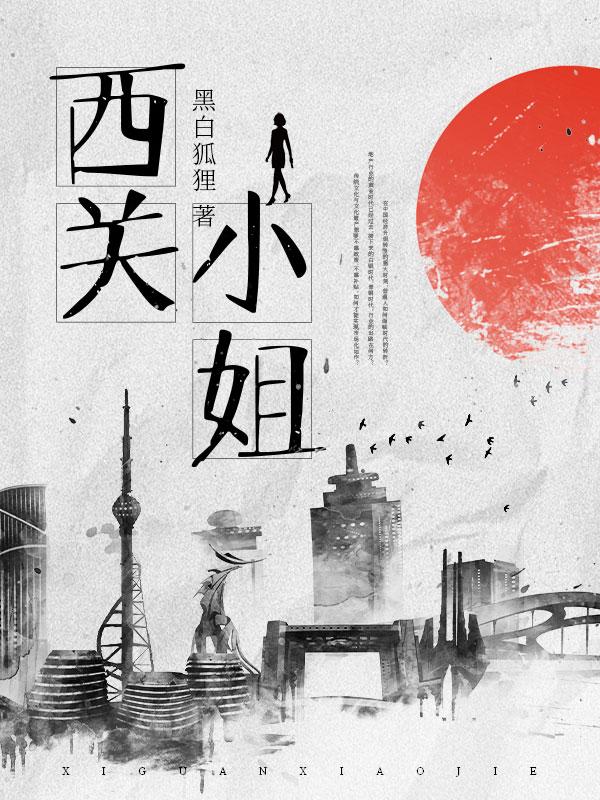青豆小说>东北糙汉捡到娇气包后 > 95100(第3页)
95100(第3页)
胡乱擦掉的泪痕糊弄满脸,又麻又辣。
这便是软肋,孙平没见过这样生死相许的感情,不清楚两个男人之间浓厚纠缠的爱。
他只看到被千万事压不倒的陈建东,此刻守着关灯时,佝偻的背,像老了,又像是脆弱了,痴痴的护着这个能哄他活下去的命根。
陈建东就坐在病床边守着抹眼泪,时不时叹气,偶尔皱眉,担心他的手凉,又怕他麻药过了时间醒不过来。
后来还是阿力看不下去说了一句:“灯哥醒了看着这样不得心疼啊,洗一把脸。”
陈建东这才僵硬的起身上卫生间去擦了脸。
对,关灯爱干净,肯定不稀罕他埋拉巴汰的样儿。
手术后关灯在麻药劲后只短暂的醒了几分钟,瞧了瞧陈建东后便又深深睡过去。
“哥在呢,”陈建东轻轻握着关灯的手,柔声告诉他,“哥就在这陪着你,哪也不去,睡醒了什么时候都能瞧见哥。”
关灯沉沉的睡着,指尖却和他勾着,在醒来的几分钟仿佛撑着所有精神和陈建东牵手。
关灯做了很长很长的梦。
梦到他和陈建东第一回在凌海工厂里要债的时候,他从小没受过大伤,脑袋上破着血口子,陈建东也一身血,俩人走路互相搀着,一瘸一拐的上了三驴蹦子。
吹着如刀子般的海风,天空灰灰的。
干涸龟裂的海床上停摆着破旧轮渡,陈建东指着外头让他看。
他问——“看啥?”
陈建东说——“你不没看过海吗?那就是。”
在凌海生活十几年没看过的东西,陈建东带他瞧了。
关灯是没见过海,所以面对无边无际的海面,海风吹不开的眼瞧不清,只有海面上折射的太阳光,那时候他想「海边好像不过如此」
其实不是大海不过如此。
而是在陈建东身边,好像十几年想看的大海才变的「不过如此」
他们是对有情的苦燕子,失去了飞向南方的机会,悄悄摸摸的在旁人眼皮子底下搭窝取暖,准备这样幸福过一辈子。
苦日子也是甜日子。
只要和对方在一块,那就是好日子。
关灯彻底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的事,陈建东熬了太多天,趴在病床旁边睡着了。
关灯醒来也没打扰他,而是转动着眼珠,尝试着动弹手指,将小拇指和他哥的小拇指贴在一起。
小拇指动了动,肌肤划着男人的那一小截手指,在他沉睡中贴近,勾起,等着时间慢慢过去。
陈建东睡的很浅,被他贴了一会感觉到细微变动,乍然醒来。
他惊喜的和关灯对视着,隔着氧气面罩亲不到脸,陈建东便握起他的手,亲着他的手背,奔三的男人,在十四岁身无分文离开家乡时也从未流过一滴眼泪,此刻却像个受了委屈的青涩男孩,眼眶红红,眸光之中有庆幸、欣喜、以及难以言喻的心疼。
他无法体会关灯手术的切痛,只想求这些事不要再让关灯体会。
哪怕用命来换,他也愿意。
孙平和阿力在陪护沙发上都撑不住睡着了。
陈建东凑过去,轻轻的用额头抵关灯的额间,俩人交换着温度,“大宝…”
术后第三天关灯就要尝试下床,防止肺炎。
止痛虽然打着,但关灯下床走的时候还是疼的浑身冒冷汗,只尝试了十分钟便受不了回到病床上。
还不敢哭,不然牵着刀口疼。
辅助呼吸机在床上躺着就要用,晚上睡觉时浑身是虚汗,最开始几天也只能喝点米汤。哪怕是米汤关灯也不想喝,食欲非常差,精神头也不好,清醒的时间一天只有几小时。
好不容易熬过第一周,撤掉了呼吸机,让关灯肺部训练很不错,人工介入成功。哪怕让关灯憋气一段时间也能接受。
等到关灯稍微好一些时,起码哭的时候扯不到伤口痛后,他天天委屈难受的掉眼泪。
眼睛肿的像两颗粉色桃尖。
最开始下床疼,陈建东求了吴医生挺长时间让他多加止疼。
后来哪怕上了止疼睡觉都是浑身虚汗,关灯爱干净,陈建东就半夜定时定点的起来给他擦,免得睡不舒服。
陈建东抽不出空回去做饭,都是阿力天天在小院里做完送来,有时候阿力忙着工地的事就让孙平送。
秦少强来几回总是买棉花糖,陈建东就不让他来了。
在医院观察了十天,刀口恢复的不错,不过关灯的手术是开胸骨的大手术,后期的长期恢复至少半年需要避免胸口遭到撞击。
吴医生查房说完医嘱后,等医生走后,关灯就着急伸手要他哥抱自己,要拉手。
他也心疼陈建东这些日子在医院里煎熬的样儿,男人瘦了不少,有时候关灯都不敢说难受,就怕他哥心疼。
陈建东都半个多月没睡过整觉了,半夜要给关灯擦虚汗,辅助翻身或者半坐睡,几小时就要给关灯看看刀口。如果消炎凝胶已经干了,他会赶紧补上。
所以当吴医生走后,他小声说,“哥,完啦。”
陈建东脸色一变,心提到嗓子眼,“哪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