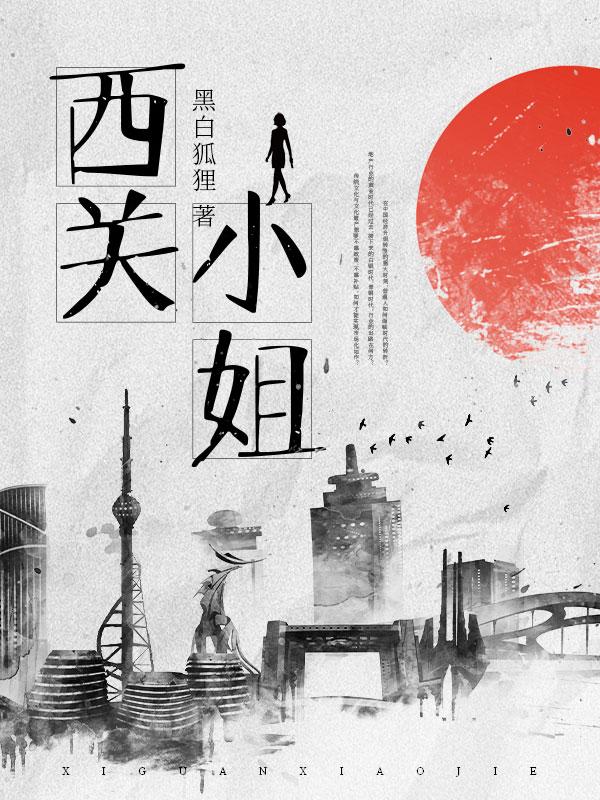青豆小说>[鬼灭] 浮寝鸟 > 第153章(第2页)
第153章(第2页)
&esp;&esp;他的动作有条不紊,像在进行某种严谨的实验操作。幸偶尔抬眼看他,发现他连整理垃圾都认真得过分,枝叶归枝叶,包装归包装。
&esp;&esp;“你做事……一直这么仔细吗?”幸忍不住问。
&esp;&esp;义勇抬头:“嗯。数据整理需要。”
&esp;&esp;“难怪中村先生说你是‘水先生’。”幸笑了,“像水一样……安静又严谨。”
&esp;&esp;义勇没接话,低头继续收拾,只是动作更快了些。
&esp;&esp;时间在雨声和剪刀声中流逝。十一点,最后一个拱门花架完成。幸长舒一口气,活动僵硬的肩膀。
&esp;&esp;“完成了?”义勇问。
&esp;&esp;“嗯。”幸看着满地成品,有种虚脱的满足感,“谢谢你,不然可能要忙到凌晨。”
&esp;&esp;义勇摇摇头,从便利袋里拿出两个饭团和两盒热茶:“吃吗?”
&esp;&esp;“你买的?”幸惊讶。
&esp;&esp;“嗯。想你可能会饿。”
&esp;&esp;他们坐在休息区的榻榻米上,简单吃了迟来的晚餐。雨还在下,敲在玻璃上的声音让人心安。
&esp;&esp;吃完后,幸收拾餐具,义勇主动去倒垃圾。回来时,他站在工作台边,看着幸洗手。
&esp;&esp;水流冲过她的手指,那枚雪片莲纹身在灯光下泛着淡蓝光泽。义勇的视线在那道旧伤疤痕上停留了一瞬。
&esp;&esp;“手……”他开口,“还好吗?”
&esp;&esp;幸关上水龙头:“嗯,只是有点累。做大型花艺时,旧伤会有点反应。”
&esp;&esp;见他有点欲言又止,幸又补充道,“不疼的。”
&esp;&esp;她擦干手,“只是会提醒我……有些事再也做不了了。”
&esp;&esp;她说得轻描淡写,但义勇听出了底下的遗憾。
&esp;&esp;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现在做的……也很美。”
&esp;&esp;幸闻言抬起了头。
&esp;&esp;“那些微缩花艺,”义勇说,声音很低,“是很精细。但你现在的花艺……有温度。”
&esp;&esp;他顿了顿,似乎在艰难地组织语言:“婚礼的花,不需要在米粒上刻花瓣。需要的是……让人感受到幸福。”
&esp;&esp;幸怔怔地看着他。这些话笨拙,生硬,但每个字都真诚得让人想哭。
&esp;&esp;“谢谢你,富冈先生。”她轻声说。
&esp;&esp;该离开了。义勇穿上外套,拿起伞。幸送他到门口。
&esp;&esp;雨还没停,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
&esp;&esp;“路上小心。”幸说。
&esp;&esp;义勇点头,推开玻璃门。冷风夹杂着雨丝涌进来,幸瑟缩了一下。
&esp;&esp;就在她要关门时,义勇忽然转过身。
&esp;&esp;他看着她,看了几秒,然后很轻地说:“早点休息。”
&esp;&esp;“你也是。”
&esp;&esp;从那天起,邮件往来的内容悄悄变了。
&esp;&esp;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三傍晚,幸关上店门时,手机屏幕亮了。
&esp;&esp;是义勇发来的邮件。
&esp;&esp;【明天降温。记得关好窗户。】
&esp;&esp;幸回复:【知道了。你也是。】
&esp;&esp;发送后她看着屏幕,忽然想起刚开始邮件往来时的样子。
&esp;&esp;那时候的邮件谨慎得像商业信函,每句话都要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