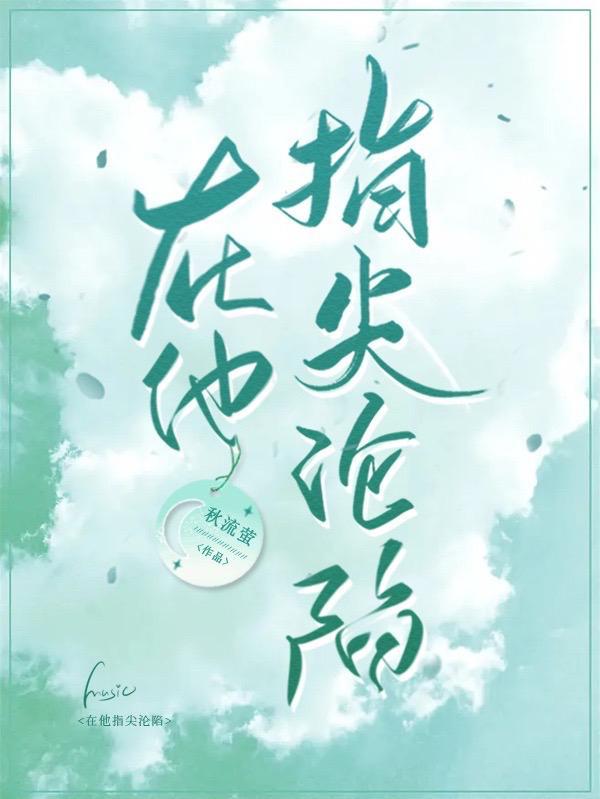青豆小说>装乖[校园+破镜重圆] > 110120(第17页)
110120(第17页)
时间要是再往前推两个小时,在她抱着花,拿着戒指,心绪复杂地纠结着要不要和顾临钊求婚时,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两个小时后,陈慧梅,她那个生理上的母亲,会推进抢救室,生死未卜。
世界仿佛在和她开玩笑。
又或者说,她这一生,就是一个巨大的玩笑。
傅叶阳并没有震惊很久。
这么多年,在傅东远手底下蛰伏,他早就学会了隐藏自己,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事,也早都发生了无数遍。
哪怕现在告诉他第二天就要世界末日了,傅叶阳或许都只是会震惊两秒,紧接着就会有条不紊地安排之后的事情。
他问:“那你什么时候走?姐,我真的不是在催你,我只是好奇。”
傅弦音说:“你居然觉得我还会再过去,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我要永远留下来了呢。”
傅叶阳说:“你还没毕业啊。”
傅弦音转过头看他。
两人视线在空中交汇。
傅弦音弯了弯唇角。
或许是因为身上都流着一半傅东远的血,这个两人在前半生都究其厌恶痛恨的东西,其实也在无知无觉的地方发挥着作用。
他们两个其实是很相像的。
一样的自私,一样的冷血。
而即便是两人都不想承认,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在这个“相像”的概括里,有时,或者很多时候,都会再增加一个人。
傅东远。
手机忽然震了震,傅叶阳低头看了一眼,而后脸上浮出一丝浅笑。
他说:“抢救成功。”
傅弦音静默地看他。
坦白来讲,她其实有些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
她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高兴于自己这个生理上的母亲终于能够活下来,还是应该遗憾于自己少年时期的噩梦病买有就此干净利落地终结。
她只是站起身,跟着傅叶阳去了抢救室。
陈慧梅的病房现在还不允许随意探护,傅叶阳问她要不要换防护服进去一下,被傅弦音拒绝了。
她说:“没这个必要。”
于是她只是站在玻璃窗外,看着病床上的那个人。
陈慧梅。
这个名字在她人生的前十余年都让她噩梦不断。
陈慧梅的尖叫让她崩溃,陈慧梅的逼迫令她窒息。
她受不了陈慧梅不停地冲她吐苦水,却每每又再次对傅东远报以希望;她受不了陈慧梅对她不管不顾的压迫,每一次尖锐的喊叫都仿佛要把她的脑袋都劈成两半。
在那一次和傅东远谈判后,看着陈慧梅被带走,傅弦音是松了口气的。
她觉得自己的好日子要来了。
可在天黑回到翡翠湾,看着家具都蒙上一层薄薄的灰尘,傅弦音却莫名地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她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或许是在陈慧梅这么多年的压迫下,出了些问题。
可即便是到了现在,眼看着陈慧梅距离死亡仅仅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傅弦音发现自己仍旧没办法纯粹地开心。
她看着病床上的人。
仪器在她身边运作着,陈慧梅双眼紧闭。她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又隔了这样远的距离,傅弦音甚至都没办法看清她脸上的皱纹是不是多了。
但她确确实实是老了。
头上的白发已经添了许多,露在被子外面的手似乎只有一层薄薄的皮。
她离得似乎是太近了,近到玻璃窗上都随着她的吐息生出了一片小小的白雾。
甚至是在来医院之前,傅弦音都在想,如果陈慧梅真的被抢救回来了,她会不会站在她的病床前,冷着脸,数落着她从前的不是,去尽情地发泄自己被压抑已久的情绪。
可真正到了这一刻,傅弦音才发现,她似乎并不想这样做了。
于是她只是看了一眼陈慧梅,而后就转开了视线。
“走吧。”
他说。
电梯里,傅弦音说:“李婵呢?现在怎么样了。”
傅叶阳的声音没什么情绪,像是在讲一个完全与他无关的人:“在北川的医院里。”
傅弦音问:“你弄进去的?”
傅叶阳说:“傅东远的意思,不过也是我做的。”
他想到了什么,有些讽意地轻笑一声:“傅东远当时为了让我一心跟着他,打了什么‘要让我亲手切断所有的软肋’的想法,安排我去安置李婵。”
![(动漫同人)[少年白马醉春风]九万里+番外](/img/9032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