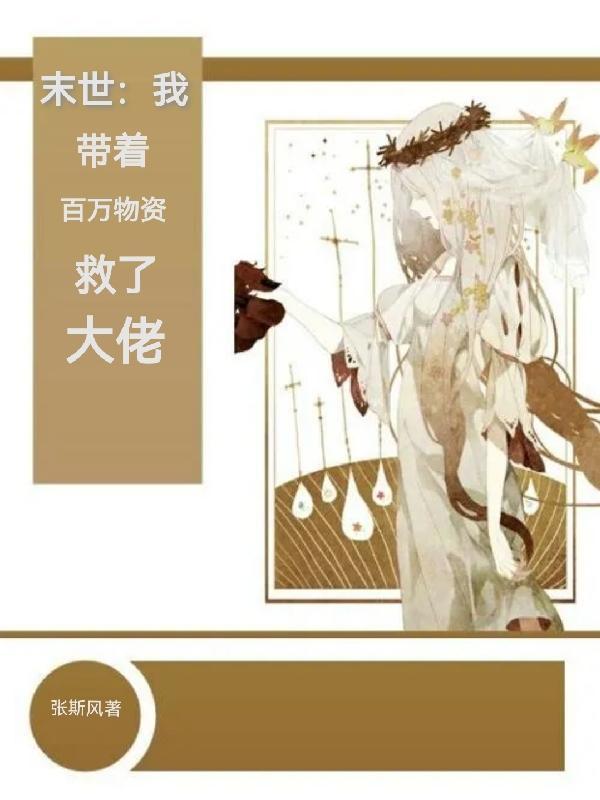青豆小说>放诞女 > 楔子(第2页)
楔子(第2页)
第一只跑掉的象叫记忆。
它带走了娜娜在老街喝咖啡乌的下午,带走了她那个总爱酗酒、身上满是烟枪味的父亲。
第二只跑掉的象叫自我。
它把那个曾在码头搬运橡胶块、皮肤黝黑的少年,连同他曾经有过的野心和羞耻,一并踩成了齑粉。
接着是爱,是时间,是所有内部听起来有力量的空洞东西。
它们倏尔鼓胀,腾飞,像飞天人头(krasue)一样,拖着血淋淋的肠肚,消失在芭提雅那泛着紫光的夜空。
“人啊,保持那可笑的、相信的姿态吧。”
命运的声音在屋角那些堆满马陆的阴影里蛊惑地响起。
手术台上的娜娜,此刻只剩下一个被重新缝合的、血淋淋的动作。
医生用镊子夹起最后一块无用的组织,随手丢进铁盆里。
那里面还躺着几块带血的纱布,在灯火下晕染开来,像极了路边摊上淋了红油、正冒着热气的猪肠粉。
我端起那盆“过去”,手心被铁盆的热度烫得麻。
走出门时,巷口外的芭提雅正如同巨蜥般游曳而至。
几个女人坐在高脚屋的阴影里嚼着甜腻的椰汁糕。
她们的脸在霓虹灯的反射下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金属蓝色。
其中一个叫露露的,正斜靠在门框上,吐出一口浓郁的丁香烟雾。她的眼神越过我的肩膀,看向那间瓦房,像滴水兽一样冰冷、麻木且空洞。
“成了?”露露问。
“成了。”我说,声音在潮湿的空气里显得干瘪。
露露冷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没有同情,只有一种看透了底牌的疲惫。
“成了就好。从此以后,她的命就是她自己的了,或者说,是谁的都行了。”
我回头看向屋里。
娜娜躺在那里,脸色苍白得像一张被水浸湿的草纸。
她杀掉了那个生出“他”的父亲,正准备带着母亲,去迎接一种如露水般易碎、却带着铁锈味的虚假快乐。
这是一次没有产房的新生,不被祝贺的分娩。
我想起北方,我的故乡。
那里有完全不同的冷,冷得人骨头脆。
阴冷的学校实验室里,空气中飘浮着一股子刺鼻的福尔马林和酒精味。
我勾着生物老师的脖子,在显微镜旁边的阴影里交换唾液。
那时候,显微镜下的细胞分裂看起来是那么有序、自然,我以为自己也抓住了那种力量,以为那是通往大人世界的、坚固的桥。
直到我被教导主任那声尖利得像划破玻璃的尖叫拽回现实。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出的那些词汇——“下流”、“不知羞耻”、“怪胎”——至今还像蜈蚣一样在我的耳膜里爬。
于是我被踢出校门,被流放到这片湿热的海岸,成了这幅亚热带画卷里一个不起眼的污点。
那时候我还不懂,乡愁是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女人的乌托邦。
我走在通往红灯区的路上。
夜晚还没正式开始,但霓虹灯已经耐不住性子,三三两两地闪烁起来,把地上的雨水坑映得像是一块块腐烂的绿宝石。
海风吹过来,带着一种沉重的、无法洗净的铁锈气息。莲花去国一千年,雨后闻腥犹带铁。
我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象,也在微微晃动。它们正盯着那些闪烁的、淫靡的灯光,跃跃欲试地想要踏出我的皮囊,奔向那片不可知的荒野。
喳喳(Buburchacha)一种盛行于新马泰地区的南洋甜品,由椰奶、番薯丁和芋头丁熬煮而成,色泽斑斓且口感粘稠。
飞天人头(krasue)东南亚民间传说中一种只有头颅、拖着漂浮内脏在夜间飞行的女性怪物,象征着某种被诅咒的、带有血腥气的自然力量。
滴水兽常见于南洋骑楼建筑排水口的一种雕塑,通常被塑造成鱼、狮或麒麟等怪兽形状,在雨季时会不断吐出积水,给人一种冰冷而寂寥的注视感。
你要是感覺不錯,歡迎打賞TRc2ousdT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八零年代之无人爱他:结局+番外冯嘉勋沈灵雁冯嘉勋沈灵雁
- 家里空的让人害怕,冯嘉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