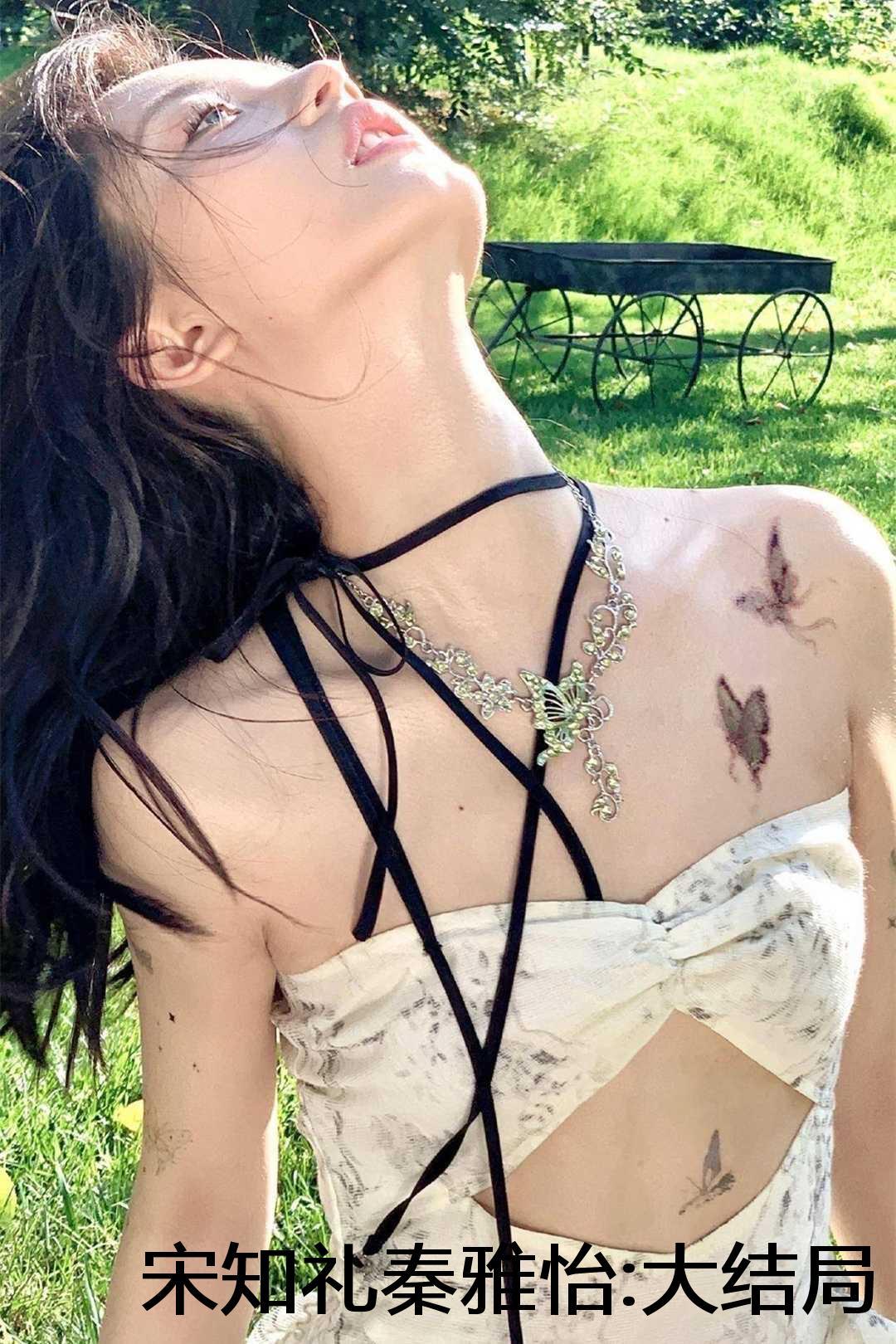青豆小说>穿越鹿鼎记,帝国无疆佳丽万千 > 第298章 长州的绝望的镜片与命运的抉择(第1页)
第298章 长州的绝望的镜片与命运的抉择(第1页)
听说明军马上要进城了!
吉川广正独自站在萩城天守阁最高的了望处,手指因用力而微微泛白,紧紧攥着那支重金购自荷兰商馆的、黄铜质地的单筒千里镜。
冰凉的金属触感透过指尖传来,却无法冷却他胸膛中翻腾的惊涛骇浪。
他将目镜紧紧压在右眼上,左眼紧闭,调整着焦距。
那层经过精心研磨的玻璃透镜,此刻仿佛成了连通两个世界的窗口——一端是绵延数百年的武家传统与骄傲,另一端则是正在将这一切无情碾碎的未来铁流。
镜筒中呈现的景象,让这位素以冷静务实着称的兰学爱好者,感到了灵魂深处的战栗。
他看到了自家引以为傲的武士——那些自幼修习剑术、熟读兵书、将“忠勇”刻入骨髓的男儿——在那些喷吐着淡蓝色尾焰、轰鸣作响的钢铁战车面前,竟然惊慌失措得像受惊的鹿群。
他们曾经整齐的阵型,在几辆“猎豹”轻型坦克的迂回穿插下,如同被顽童踢散的蚂蚁窝,瞬间溃不成形。
武士们引以为豪的具足,在对方车载射炮的短促点射下,脆弱得如同纸糊;他们试图起的、充满悲壮色彩的“决死冲锋”,往往在距离战车还有百步之遥时,就被精准的火力撕成碎片,连一声像样的呐喊都未能完整出。
他看到了那些毛利家数代人苦心经营、据险而守的山城砦垒——岩国口、玖珂口、大津郡方向的一个个据点——在对方空中力量的俯瞰与远程火力的精准打击下,命运如何。
镜筒追随着天际那些如同死神信使般的小黑点(无人机),当它们在某座砦垒上空稍作盘旋,不过片刻,那种令人牙酸的特殊呼啸声便会撕裂空气,紧接着,一团远比“国崩”火炮猛烈十倍的橘红色火球便会从那砦垒的核心处猛然膨胀、绽放!
坚固的石垣不是被“炸塌”,而是仿佛被无形的巨力从内部“撑爆”、解体!
木材、碎石、残肢断臂,混合着浓烟被抛向数十丈的高空,然后如同肮脏的雨点般纷纷落下。
整个过程,守军甚至看不见敌人的面孔,听不到敌军的喊杀,只有死亡以最纯粹、最冷漠的形式从天而降。
他看到了赖以进行长期笼城抗战的命脉——隐藏在西北山谷中的三田尻粮仓——此刻已飘扬起陌生的旗帜,那些钢铁战车如同忠诚的巨兽,沉默地拱卫在粮仓周围。
而连接萩城与西部腹地、更是通往石见银山方向的咽喉要道须佐峠,镜筒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隘口上已经搭建起了样式奇特的金属塔架(雷达和通讯天线),穿着淡青色铠甲的明军士兵在新建的工事间巡逻。
后路已绝,粮道被掐,萩城已成真正意义上的“孤城”。
更令他感到骨髓寒的,是那精准得令人绝望的炮火“表演”。
明军的重炮群似乎并不急于轰塌萩城宏伟的天守阁和厚重的主城墙。
相反,它们的火力像一位最高明的外科医生手中的柳叶刀,冷静而精确地“剥离”着萩城的防御体系。
远处山头上,属于长州藩的一个个外围支城、前沿砦垒、关键哨所,接二连三地在精准的炮击下化为齑粉。
每一次沉闷如滚雷的轰鸣传来,吉川广正都能感觉到脚下天守阁的木地板传来轻微的震颤,仿佛那炮火不是落在数里之外,而是直接敲打在他,以及城内每一个守军、每一位公卿家老本就濒临崩溃的神经上。
那种感觉,不是热血沸腾的战场搏杀,而是一种缓慢的、窒息的、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点点捆缚、扼杀却无力反抗的绝望。
“呼……”吉川广正缓缓放下千里镜,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那气息在初秋微凉的空气中凝成一团白雾。
他的手心全是冷汗,与黄铜镜筒接触的地方一片滑腻。
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凭借萩城复杂的地形、毛利家武士的血勇、以及长期笼城战术或许能与敌周旋、等待渺茫“转机”的幻想——如同阳光下的朝露,在这一刻彻底蒸殆尽,连一丝水汽都没有留下。
镜筒中呈现的不是“战争”,而是“处刑”。
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降维打击式的处刑。
他清晰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无论选择等待那虚无缥缈的“神风再临”或“幕府援军”这可能性已趋近于零;还是响应宍户元次等老臣“玉碎报国”的狂热号召,结局都早已被那只高悬九天之上的巨手注定。
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长州藩,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连同其上的数十万生灵,将要付出的代价——
是部分毁灭,还是彻底、不留一丝痕迹的湮灭?
家族的延续、领民的生存、毛利氏血食祭祀的不绝……这些远比空洞的“武士名誉”更沉重的责任,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头。
不能再犹豫了!
必须行动,必须抢在一切无可挽回之前,抓住那最后可能争取到的、相对“体面”的出路!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哪怕这条路上布满荆棘与屈辱,也远比通往悬崖的绝路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