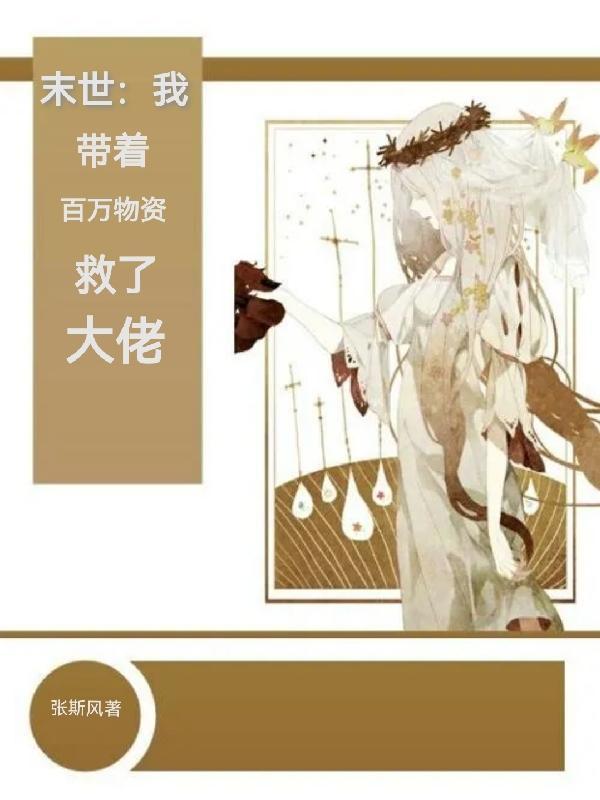青豆小说>天汉风云 > 第21章 司马深机定阴谋宋郭策陈邺水寒(第4页)
第21章 司马深机定阴谋宋郭策陈邺水寒(第4页)
这种向心力,甚至过了当初对张角的盲从。
张宁薇暗暗握紧了拳头。
不管孙廷萧想干什么,她只认准了一点——若是他真的为了所谓的大局,要把玉澍妹妹双手奉上给安禄山那个淫贼,那她这个曾经一起颠鸾倒凤过的“好姐姐”,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去帮那个狠心的男人解决掉这个“烦恼”,绝不让玉澍受辱。
就在这时,一名小医女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喊道“圣女!圣女!苏太医那边传话来说,大贤良师……大贤良师他醒了!”
自广宗总坛被救回后,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大贤良师”张角,便一直如同活死人般沉睡不醒。
虽说脉象平稳,呼吸尚存,但无论张宁薇如何呼唤,都毫无反应。
苏念晚为此可谓是殚精竭虑。
她翻遍了医书,又在军中四处寻访,终于从一名参加过西南战事的骁骑军老卒口中,打听到了这种类似“离魂蛊”的症状。
据此,她大胆施针用药,前两日张角忽然呕出了几口腥臭难闻的黑水血块,随后又陷入了更深的沉睡。
谁曾想,就在今日大家都忙着各自差事没注意的时候,他竟然真的醒了过来。
消息传到城外,孙廷萧连马都顾不上换,一路狂奔从新军训练场赶回了邺城驿馆。
一进驿馆后院,只见里里外外已经被闻讯赶来的黄天教渠帅和核心教徒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些人个个神情激动,有的甚至还在抹眼泪,见孙廷萧来了,纷纷自觉地让开一条道路,眼神中满是敬畏与感激。
孙廷萧大步流星地走进厢房。
只见张角已经靠坐在床头,虽然脸色依旧苍白如纸,形销骨立,但那双曾经浑浊的眼睛此刻却已恢复了几分神采。
张宁薇正坐在床边,手里端着一碗热粥,一边小心翼翼地给他喂食,一边止不住地掉眼泪,那是喜极而泣的泪水。
苏念晚则静立在一旁,神情专注地为张角号着脉。
见孙廷萧风尘仆仆地闯进来,她转过头,那张温婉娴静的脸庞上绽放出一个令人安心的温柔微笑。
“将军放心。”苏念晚轻声说道,语气笃定,“大贤良师体内的蛊毒已去大半,脉象虽虚但已回稳,应当是无妨了。只要接下来安心休养,进补得当,下地走动也就是这几天的事。”
苏念晚此话一出,就像是一道赦令。
张宁薇手中的动作一顿,连忙放下碗勺。
她转过身,竟是当着满屋子人的面,双膝一软,“噗通”一声跪倒在苏念晚面前,泣不成声地说道“苏姐姐!多谢你救我父亲性命!此等大恩大德,宁薇……宁薇没齿难忘!”
苏念晚见状,连忙弯下腰去搀扶,嘴里连声说道“圣女快别这样!医者仁心,这都是我分内之事,哪里当得起如此大礼!”
可张宁薇此时情绪激动到了极点,连日来的担忧、委屈与如今的狂喜交织在一起,让她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了一般,软绵绵地根本站不起来。
她一边流着泪,一边又转向刚刚进门的孙廷萧,跪在地上欠身行礼,声音嘶哑“宁薇……还要谢将军深入虎穴,救我父亲脱困!若无将军……”
“哎哎哎!行了行了!”孙廷萧最见不得女人这副模样,尤其是自己的女人。
他一个箭步冲上前,不由分说地伸出有力的双臂,一把将瘫软在地的张宁薇给架了起来,然后扭头冲着旁边的马元义吼道“还愣着干什么?快搬个凳子来给圣女坐下!”
安顿好张宁薇,孙廷萧这才转过身,凑到床边,俯下身子,近距离地观察着这位大贤良师。
张角那张枯瘦的脸上满是病容,嘴唇微微翕动着,喉咙里出风箱般嘶哑的气声,断断续续地挤出几个字“谢……谢……救命……之恩……”
孙廷萧轻轻按住他想要抬起的手,温言宽慰道“大贤良师不必多言,也不必费力说话。您只管安心将养身体便是。如今广宗的叛徒唐周已除,黄天教内部已经安定。那些信奉您的百姓,我们也已经放了钱粮种子,妥善安置。朝廷这次是真心想要善待大家,绝不会再让大家流离失所。”
听到这番话,张角那双浑浊的老眼中再次涌出了泪水。
他颤抖着伸出枯枝般的手,指了指坐在旁边的女儿张宁薇,又指了指孙廷萧,眼神中满是托付与感激。
张宁薇明白父亲的意思,连忙上前握住父亲的手,将其轻轻放回被子里,柔声说道“爹,您放心,别费力气了。女儿……女儿定会好好报答孙将军的大恩大德……”
说到“报答”二字时,她的脸颊微微泛起一抹红晕,眼神不自然地飘向了孙廷萧。
那可不是要报答的吗?
连清白身子都已经给了这位孙将军嘞!
当然,当着这么多教众和部下的面,此刻自然还不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的时候。
夕阳西下,余晖透过雕花的窗棂洒进玉澍郡主居住的院子,将那些堆积如山的礼物镀上了一层金红色的光晕。
这些礼物都是这几日安禄山陆续送来的。
红木箱子、缎面匣子、漆器盘盏,满满当当地占据了厢房的大半个角落。
有北方的狐裘貂皮,有西域的珠宝玉器,有东海的珍珠玛瑙,还有南方的绫罗绸缎,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珍品。
玉澍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便让侍女们将这些东西随意堆在一旁,连看都懒得多看。
她现在关心的,是那几箱从长安带来、由圣人御赐的红妆衣衫。
侍女们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取出那些精美的嫁衣、凤冠霞帔,在她面前一一展开,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大喜之日”。
孙廷萧与安禄山约定送亲的具体时辰地点,已经通过鹿清彤转告了她。
按照流程,再过三日,她就要盛装出,前往邢州,然后……嫁给那个肥得像头猪的安禄山。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八零年代之无人爱他:结局+番外冯嘉勋沈灵雁冯嘉勋沈灵雁
- 家里空的让人害怕,冯嘉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