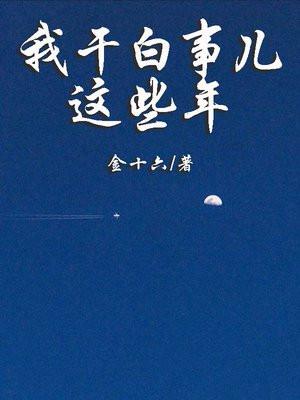青豆小说>她的小戏子GB > 第81章(第1页)
第81章(第1页)
署令陪着笑说:“臣愿意为军使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军使大?人等很久了吧,茶一定凉了,”他抬高声音向外面呼喊,“还不去给?军使大?人换一盏,马上摆宴,上好酒好菜招待。”
杨玄礼站起?来一笑,不慌不忙道:“张大?人这是把我当做了土匪,唐朝的官员对于不入流的土匪才会说要拿好酒好菜招待呢。”
他的神?色微凛,目光淡泊到看不出来变化,那双眼睛不笑也好看极了,笑一笑犹如灯下的鬼魅,他不屑地撇嘴,“本大?人不稀罕,”
“我确实?想要一样东西,却不是张大?人家?里?的好酒好菜,那等俗气?之物?,张大?人还是留着自己享用吧,本大?人另有所?爱。”
署令擦了擦汗,无奈地跪转着哀求他,追随着他的脚步信誓旦旦道:“大?人请讲,只有你要,”
“只要臣有,”
“臣什么都愿意给?你。”
杨玄礼回头一笑,展颜道:“当真??当真?什么都愿意给?我?”
署令站起?来,点头哈腰,“当真?,当真?。”
杨玄礼俯视他,从容不迫地笑:“我要令爱。”
署令僵在原地,他这是什么癖好,他会不会有奇怪的癖好,像是担心他一遍听不懂,杨玄礼又好心地给?他重?复了一遍,“张大?人没?听清楚吗?我说我要你女儿。”
署令虽然圆滑世故,在官场上左右逢源,而且十分爱惜自己的羽翼,不愿意有一点舍弃,向着钻营和高攀孜孜以求,但他爱自己的女儿,杨玄礼是炙手可热的权贵不假,许多官员为了升迁争相向他纳贿,跪着求着要把女儿献给?他亦不假,可那人绝对不是他,在他眼里?,这就?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再者杨玄礼接纳了那些女子也是转手随意送给?别人,他虽则从不沾染,却对人命是如此无情冷酷,女儿给?他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署令瞪大?眼睛,很艰难地吞咽一下,声音干涩道:“臣只有一个女儿……”
“臣有三个儿子……”
“臣可以用儿子换女儿……”
杨玄礼打断了他,坚定不移道:“我就?是要你女儿,我要拿她来试药。”
与此同时,两仪殿内,两个人正在解衣,打算睡下。
每次就?寝,总是她先缩到床角瑟瑟发抖,他站在床外散漫地脱衣,眼神?总是不离她,缓慢地寻找一个机会把她拖到怀里?。
他今天没?有明确答应医师的话,徐直看着他,看着他,眼皮轻阖,恐惧失措地抱紧自己,看着他落地的腰带,呼吸越来越急促,他眼底的欲色越来越浓。
怎么办,怎么办,她欲哭无泪道:“医师说了需要休息。”
他亦不是不想让她休息,他实?在是在客观地评估她的极限在哪里?,那些医师们最喜欢站出来说一些夸大?之词,显得自己与众不同,以邀直名。
在他看来,他们明明越来越契合,做完一向都很畅意,如果不是她想要自己,他在床上一向也没?那么过分吧?怎么就?变得脆弱了?
李泽一边脱衣一边想,“还是要多做,不能?给?她惯出毛病,”
“倘若得了势,不得天天拿着医师的话来压自己。”
他一如往常地沉冷道:“过来。”
徐直不看他,眼神?恍惚也不知道落在了哪里?,她无助地抱着膝盖流泪,嗫嚅着摇头,“我不过去,医师说了要休息,”
她抽泣着哭,“我太疼了,我想休息,求你,”
“连医师都知道要让我休息……”
李泽抛开最后一件衣服,跪上床对着她,丝毫不为所?动,苛酷地命令她:“不要让我说第二次,自己把腿缠上来。”
身?体的反应比脑子要快一步,她已经形成反射性习惯了,即便怕的要死,也立马打开双腿缠上去,与他的膝盖相抵,徐直流着长泪依然不死心地在劝他求他,“放过我吧,真?的,”
“我感觉我要死了,”
李泽调整她双腿的位置,眼里?的情绪全部被本能?的y望代替,他不想再听她多余的话,伏低捧住她的脸,一边亲她一边帮她脱衣。
徐直仰着脸闭上眼,害怕崩溃地大?哭。
李泽吻着她的眼泪,哄着她耐心极了,“三娘听话,放松一点就?不会死。”
藩镇(五)
后半场,她?渐渐在他怀里晕过去,李泽停下来缓了缓,感到?她?体内异样的热度,o露在锦被外面的整片肌肤,透着汗湿的粉色。
他去探她?的额头,才知道?她?所言非虚,的确是?有?点发烧了。
帮她?穿好衣服,下了床吩咐宫婢去催促太医署的人?过来。
今天晚上正在太医署值班的博士恰好是?裴令仪,他又?随着其他两个值班的医正过来两仪殿,那两个医正上了年纪,这般折腾来去不免气喘吁吁,裴令仪虽然年轻,但是?博学多识,手法娴熟,所以全程大多是?两个医正在一边指导,他一个人?忙碌。
陛下穿着寝衣把娘娘抱在怀里,隔着帷幔,能看到?他似乎在给娘娘擦脸上的汗水,平淡的语气跟外面的人?说:“把她?最近喝的药全部拿去,仔细检查,重新评估她?的体质,出具新的药方?,”
“务必要迅速,马上帮她?退烧。”
李泽沉吟一会儿,又?说:“去把张署令叫来。”
死东西,不是?说好了他研制出来的药绝对没有?副作用吗?胆敢糊弄他,平白无?故就这般发了烧在床上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