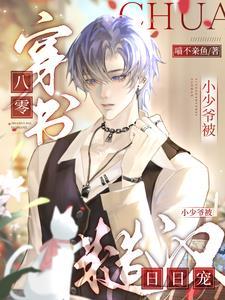青豆小说>美强惨的水仙[重生] > 第13章 经年(第2页)
第13章 经年(第2页)
紫宸殿中回荡着他忠心劝阻的声音,皇帝面色微缓,赵康察言观色下在一旁坐不住了。
“太师这些话,梁昌等人难道不知道吗?他们这时候上书,不就是借此为难陛下吗?若是不加惩处,人人如此,朝廷如何协助陛下治理江山?顾太师把先帝搬出来,怕是不顾陛下此时的难处吧。”
赵康这番话说到皇帝心坎里去了,此等逆臣就是专门来刁难朕的,怕是还对当年的事心怀怨愤。只恨时日太短,他手下的武将青黄不接。
可这番话也引来了顾太师的怒目而视,他眉头紧皱冷哼出声,直起上身甩了一下袍子,眼中满是对此等佞臣的鄙夷神色。
“老臣可不知,还请左丞大人和老臣细说一番,梁昌等人是陛下的臣子,忠心事君多年,又为什么要为难陛下?又究竟是为什么才会上这道折子?”
就是你个狗东西一意撺掇,才让陛下早早对楚家下手。你那姻亲表妹还在宫中处处刁难三皇子,怕是事情都传到北地去了。梁昌他们为了什么上书施压,朝中怕是人尽皆知。
“你!”
“好了!”
皇帝紧闭双眼,似是被两人的争执吵醒了一般,用手扶着额头很是疲惫。
他何尝不知这两人是在自己眼前故意这般争论,又何尝不知他们心中各自的打量。可顾太师说得确实有道理,若是这个节点把梁昌他们都给换了,风声一旦漏出去,怕是要不了多久就得准备打仗了。
这些年朝中不稳,民间也是灾乱频出,国库空虚如何承担战争的消耗。
“朕知道太师的意思了,都下去吧,让朕好好想想。”
赵康自然是心有不甘,若是今日顾太师没来,他有九成的把握让皇帝就此把军权收回来,到时候再派一二亲信前去北地,那十万大军岂不是手到擒来,大权可期啊。
毕竟是三朝元老,在皇家的脸面是他这种后起之秀比不过的。
只是萧妃那边怕是又得好生安抚一番,否则再生事端就麻烦了。
翌日,宫中传旨,驳回了梁昌等人乞骸骨的请求,御使带着大量赏赐浩浩荡荡出了皇城,往北地而去。
宫中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皇帝不知怎的,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个勤敏好学的三皇子,将其传唤到紫宸殿好一番嘘寒问暖。后宫赵昭仪命人把皇子所内的问心院上上下下整修了一番,添置了许多东西。
三皇子似乎又回到了昔年备受长辈关爱的地位。
“裴哥哥。”纪绡的眉目间满是愁绪,他有些担心这般高调会引来更多事端,同时也有不解:“我听说梁昌将军他们前些日子上书请辞了,最近这些是否与他们的奏折有关?”
裴青最是看不得他这般小心翼翼的样子,心中不免对以往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又恨上几分。
“殿下可还记得臣当日所说,殿下出身高贵,便是天大的尊荣也配得上,如今不过是些许对殿下的补偿罢了,何须要如此担忧呢?”
树大招风是不假,可若是盘根错节枝干虬劲,便是狂风又如何能吹得动。
梁昌等人本就是跟随大将军征战四方才得来今日的地位,不过一步不危及性命的险棋罢了,早日将这些纷争搬上台面,总好过任其如同暗疮一般在见不到的地方愈演愈烈。
“殿下若要争,就该明白,有些事是必然要做的。”
纪绡心中何尝不知,但他毕竟还怀着几分稚子之心,希望这世道永远保持平和稳定。
只是看着裴青从容不迫的样子,虽不知为何他身上会有这种久经雨雪风霜的稳重淡然,纪绡也慢慢放下心来。
建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漠北派军偷袭晋朝边城云安,然北地驻军提前接到密报,准备充足设下埋伏,此战共斩获漠北袭军两千一百三十余人,云安城固若金汤未有分毫闪失。
漠北异族未能劫掠到物资,又恰逢五十年一遇的极寒降温,部落死伤惨重元气大伤,无奈远迁,龟缩于草原深处休养生息。
自此战之后七年内,再无大规模犯境之举。
梁昌戍边有功,封镇北侯。
……
一晃经年,已是建元十年的七月份。
皇城西侧的永延殿。
永延殿正厅内,地上铺着净亮的黑色宫砖,绕过门口的丝质云屏,屋内有淡淡的果香,堂内摆设清雅素净不见金奢玉靡,边角处放着几缸青绿翠红的碗莲,正安静盛放着。
伴随着太监们的通传,一名身着月白对襟窄袖长衫的少年走了进来,衣襟处用宝蓝色的丝线滚着祥云蝠纹,行动之间腰上的犀带微微摆动。
那少年虽则生了一张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的俊美面孔,却身如青松气质雍容清贵,生生将面容上的昳丽艳色压下,只余清雅高华。
“祈安呢?”
他扭头问身边的随从,声线温润如玉。
在三皇子身边服侍了将近七年,王山脸上挂着恭敬熟稔的笑意:“裴大人今日告假出宫了,算算时间,也快该回了。殿下今日在校场习箭想必也劳累,奴才叫人备了些降燥的汤水,殿下不妨先用一些。”
纪绡口中低声抱怨一声:“又出宫。”
主子的话王山只当没听到,热络地招来宫人帮他换了身松快的衣服,摆好了汤水茶点。
精致的青花缠枝瓷碗中汤水清亮微翠,一眼望去就让人觉得舒爽,小太监在一旁轻揉纪绡肿痛的肩颈,在校场站了一天的疲累也去了几分。
“这汤留着,等祈安回来了我和他一起喝。”
想到那人怕是也忙了一天,纪绡也没什么胃口喝这汤水,只饮了几口温茶。
他一口一个祈安祈安的叫着,下人们也见怪不怪。自打裴大人二十岁冠礼没找旁人,违背了规制只让三皇子为他取字,祈安这个名字就成了三皇子话中的常客。
反正旁人是不怎么敢这么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