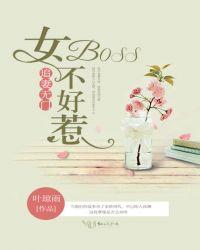青豆小说>从棺材里捡了个老婆 > 4050(第29页)
4050(第29页)
“那就先谢过各位婶婶了。”
池也一脸感激,甚至还有些庆幸。
但她听到后天还要摆宴席,心中犹豫不决。村里有些人她都不认识,难道要把几十户人家都请来吗?
好吧,她其实就是不想请池家大房一家。
她可不想在大喜的日子看到那一张张倒胃口的脸。至于其他人,只要是真心实意来祝贺的,她都欢迎。
“上梁那日要请多少人?”
李巧云仔细想了想,答道:“我们就请一些村里关系好的人家,还有那边的泥工瓦匠,大概也就几十号人。”
池也心中有了底,笑道:“行,到时候让他们把家里人都带来,办得热热闹闹的。”
“还有,上梁那日需要置办的东西,三婶尽管去买,或者我明日从城里带回来也行,银子的事不用担心。”
闻声,李巧云假意瞪她一眼,道:“该省还是得省,有钱也不能乱花。”
池也浅笑不语,多亏了空间农场,这些天她赚了不少银子。
如今她已经彻底摆脱初到此地的窘境,手头宽裕了不少。
“行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别在这碍手碍脚的。”
“那三婶,我和青宛先回去了。”
说罢便牵上沈青宛的手往家走。
几位妇人看着池也和沈青宛并肩离去的背影,只觉分外美好。
“池也这丫头真是越来越好了。”
“谁说不是呢,这都盖上大房子了。”
至于盖房子的钱,李巧云夫妇对外只说,池也在城中遇到了贵人,那贵人为报答救命之恩,便给了她一些银两。
村里人时常有人凑到李巧云面前问长问短,但李巧云不肯多说,每次都以寥寥数语糊弄过去。
久而久之,村里人觉得无趣便作罢了。反正问了,银子也到不了他们手中。
“巧云啊,”其中一位更为年长的妇人面上的笑意收敛了些,转头看向李巧云,认真道,“池也的年纪也不小了,她的婚事你也得张罗起来了。长顺夫妇走得早,大房那一家子又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你这个婶婶可得好好给她把把关。咱总不能因为一个烂人耽误了一辈子吧。”
王升那一家子当时大张旗鼓地前来退婚,闹得整个村子沸沸扬扬。
她们几个对池也投河那事至今心有余悸,是真的心疼池也,说的话也皆是发自肺腑。
李巧云显然也记得王升这事,脸上的笑意瞬间隐去,眉眼间也多了几分厌恶与忧愁。
厌恶是对王升的,忧愁是对池也的。
她犹记得嫁入池家时,池也尚在牙牙学语,自己看着她一点点长成如今这般模样,自然十分心疼池也的遭遇。
想到这些,李巧云对王升的恨意又多了几分,当然还有王翠兰。
王升是王翠兰的娘家侄子,那时王升还不是举人,王翠兰便极力撮合二人,说什么亲上加亲那种冠冕堂皇的屁话。
其实不过是王家尚有些钱财,王翠兰起了贪念,想私吞了池也的聘礼。
那王升不过是走了狗屎运,在乡试放榜时,名字出现在榜单的最后一位。
有了举人的身份,王家整日一副鼻孔朝天的模样,觉得池也配不上他们家的儿子,便萌生了退婚的意思。
若当时王家痛快退了婚,“池也”也不至于拖到这个年纪。
可偏偏他们骑驴找马,低了王家看不上,高了别人又看不上王家。
直到池长顺因病去世,王家不知因何缘故才来退了婚,毕竟也没听说他们与哪家定了亲。
李巧云心中百般滋味,脸色变幻莫测,最终只余下一声叹息。
这事还是得找池也商量,她不能擅自做主。
众人见她情绪不高,心中皆是一阵叹息。
沉默过后,几人又说起沈青宛,道:“青宛姑娘应当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吧,她头上的金簪亮闪闪的,肯定值不少银子,怎么会一直住在我们村子里呢?”
李巧云对其中的细节不甚清楚,只道:“青宛家里出了点变故。”
妇人们又是一阵叹息,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两个好好的姑娘,怎么都遭遇了不幸。
池也和沈青宛可不知道外面的妇人们在为她二人的遭遇唉声叹气。
两人一进到屋里,池也便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沈青宛。
“给。”
这些日子,池也每次从临江城中归来,总会带些东西。有时候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有时候是一些饰品。
沈青宛对此见怪不怪,但每次仍会为此感到惊喜。
她打开外面裹着的一层布,里面躺着一叠手帕。
之所以说是一叠,是因为池也一口气买了十条,颜色、花纹各不相同。
沈青宛觉得有些好笑的同时,心底涌起一阵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