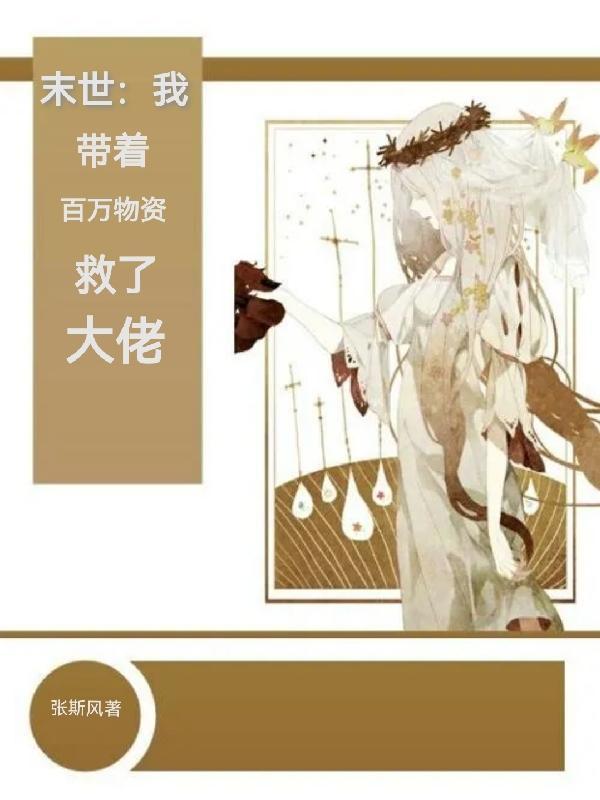青豆小说>四合院:整治全院,都跪求原谅 > 第235章 又是哪门子的妖精出幺蛾子了(第1页)
第235章 又是哪门子的妖精出幺蛾子了(第1页)
空气似乎顿时凝滞了。四合院里原本懒洋洋的气氛被这突如其来的喧哗搅得四分五裂。各家各户的门缝里,慢慢探出了一只只睡眼惺忪的脑袋,有的打着哈欠,有的皱着眉头,更多的是那种等着看热闹的八卦神情。
何雨柱眯起眼睛,低低啐了一口,心里暗骂了一声:“又是哪门子的妖精出幺蛾子了。”
他慢吞吞地收回视线,本打算绕开这场闹剧,低头从角落里抄近道去食堂。可耳朵里,贾张氏那一声声高八度的叫骂像是长了钩子,硬生生把他的注意力勾了回来。
“这可是老娘传了一冬天的棉裤啊!昨儿个晾在窗台底下,今儿一早竟然被扔到了垃圾堆里头!你们哪家没人教养的王八羔子干的好事?!站出来,给老娘赔裤子!”
贾张氏的嗓门又尖又利,带着北方女人特有的泼辣与强横,刺得院子里的鸟都扑棱棱飞起。她那张横肉堆叠的脸上,写满了愤怒与委屈,眼角的皱纹仿佛都在颤抖。
何雨柱嘴角微微一抽,心里暗道:“真特么晦气,一大早就听这破锣嗓子。”但转念一想,贾张氏这副德性,要是没人理她,保不齐得嚷嚷一上午,到时候吵得食堂也干不了活,倒不如现在就解决了,免得误了正事。
他将手里的饭盒随意往旁边一放,叼着烟头,大步流星地朝东厢房走去。鞋底踏在青石板上,出沉闷的啪嗒声,每一步都仿佛敲打在人心尖上,引得周围观望的人群微微一动,像湖面被石子打破的涟漪。
“得了得了,吵吵啥呢,大清早的,邻里邻居都还没睡醒呢。”何雨柱站定在贾张氏三步之外,抬手摘下烟头,弹了弹烟灰,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烦,却又不得不装出一副耐心劝解的模样。
贾张氏一见是何雨柱,气势顿时更足了,像是找到了出气筒。她叉着腰,怒目圆睁:“柱子!你瞧瞧,你瞧瞧!这四合院里也不就你们几个男人手脚最脏!是不是你?是不是你闲得蛋疼,把我衣服扔的?!”
四周围观的人立刻窃窃私语起来,目光在何雨柱身上流转,有怀疑的、有看笑话的,也有暗自幸灾乐祸的。
何雨柱被这莫名的指控气得笑了,鼻孔里喷出一声冷哼:“贾张氏,你嘴巴放干净点!老子一大早忙着送饭盒,哪有闲工夫碰你那破裤子?谁稀罕动你家破烂啊?”
贾张氏却不依不饶,指着他鼻子骂:“你别以为你做厨子的,就能嘴巴油滑!四合院里要数你最不安生,别是你心情不好,见谁晾点东西就心里酸,动手给扔了吧!”
何雨柱眼神微微一沉,眸子里浮起一丝冷意。他慢慢直起身子,身形高大魁梧,在这小小的院落里,像一堵活生生的墙。他的气势一涨,周围嘈杂的窃窃私语顿时一滞,空气仿佛都稠密了几分。
“贾张氏,”他咬着牙,声音低沉如压抑着的雷霆,“你再胡说八道一句试试?”
他身上那股从小在街头巷尾打滚出来的狠劲子,像锋利的刀子般逼得贾张氏后退了一步,眼中闪过一丝惧意。但她是那种嘴上绝不肯认怂的泼妇,硬是梗着脖子,哆嗦着嘴角骂道:“老娘就说了怎么地?不是你,就是你们这些野小子干的好事!”
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一旁一直默不作声的秦淮茹终于忍不住了,她提着一篮湿漉漉的衣服,小心翼翼地走上前,轻声劝道:“柱子哥,张姨,别吵了……大伙都是邻居,有话好好说……要不,咱先找找看,兴许是小孩儿们玩闹,把衣裳不小心弄掉的呢?”
何雨柱听了,心里微微一动。他低头沉思了一瞬,心中冷笑:秦淮茹这娘们,嘴上说得好听,八成巴不得自己跟贾张氏闹翻,到时候自己名声臭了,食堂的活计也保不住,倒便宜了她们家。
可面上,他只是冷哼一声,懒得跟这帮人计较。他抬眼扫了一圈围观的人群,目光如寒刃般逐一扫过。那些原本还想看热闹的人,被他这么一瞪,纷纷低下头,装作忙着自己手里的活计。
何雨柱走到东厢房窗台下,蹲下身子细细查看。泥地上有几个小小的脚印,看大小,分明是孩子们踩出来的。他顺着脚印看去,果然在院墙角落的一堆杂物堆旁,现了一只破旧的小木凳,上面还残留着几根彩色的棉线。
他伸手一捞,提起一件半湿的儿童棉袄,皱眉低骂了一声:“妈的,果然是那些皮猴子干的!”
背后,贾张氏还在喋喋不休,嘴里骂骂咧咧个不停。她的声音尖锐刺耳,像夜里不肯停歇的耗子,在人耳边啃咬着,让人心烦意乱。
何雨柱猛地站起身,扭头冲着围观的人群喝道:“棒梗!小当!出列!”
人群一阵骚动,两个瘦瘦小小的身影战战兢兢地从人群后面挤了出来,一个是棒梗,另一个是小当。两个小孩满脸的委屈和害怕,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不敢直视何雨柱那双冒着寒光的眼睛。
何雨柱双手叉腰,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声音低沉得像滚动的雷霆:“说!是不是你们偷着玩,把贾张氏的衣服给扔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棒梗抖了抖,小当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被旁边怒目而视的贾张氏瞪得哆嗦了一下,哭丧着脸,咬牙跺脚:“是……是我们不小心踢翻了凳子……衣服掉地上……就……就被风刮到垃圾堆那边去了……”
话音落地,院子里一片死寂,鸦雀无声。众人的目光在棒梗和小当之间游移,带着几分幸灾乐祸,也有几分了然。
何雨柱深吸一口气,胸膛一鼓一鼓的,像是压抑着火山喷的怒气。他慢慢地转过身,冷冷地看着贾张氏。
“贾张氏,你听见了吧?不是老子干的,是你们自家的孩子皮,闹腾出来的好事。”
贾张氏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像极了冬日里墙角霉的旧棉被。她张了张嘴,想要狡辩,却现四周人群的目光都带着隐隐的鄙夷和嘲讽。那种无形的指责,如同一条条细小锋利的针,扎得她脸上火辣辣的。
这串名字,像串在绳子上的锈钩子,一旦拉开,必定带出什么来。
他坐在那里,夜深无声,墙角的小灯泡出“滋滋”的响声,仿佛也感知到了那层潜藏已久的隐秘。
第二天一早,天还未大亮,院子里氤氲着雾气,徐峰早早起了身。他没像平时那样先烧水洗脸,而是直接换了件不惹眼的深灰色旧布衫,把那本记满线索的黑皮笔记本塞进上衣内袋,一路踏着尚未退潮的露水出门。
骑上自行车时,他没走正路,而是从胡同北口绕了个远圈,避开了早起买菜的邻里。骑了不到二十分钟,他拐进了厂区后巷,停下车时,周围还是一片静谧,远处锅炉房刚开始作业,白烟悠悠爬上了天。
徐峰没有走主楼,而是朝仓储办公室那栋偏西小楼走去。小楼门前落着一地枯叶,窗台上的铁栏杆已经锈出小孔。他轻轻推门进去,脚下的木地板吱呀作响。
“谁啊?”里面传来老周特有的鼻音嗓门,带着点不情愿的慵懒。
“我。”徐峰推开门,站在光影交错的办公室门口。
老周正背着他,蹲在地上翻着柜子里的文件,头已经稀疏,脖子上挂着一根蓝色毛巾,听见声音回过头来,眨巴着眼,掩饰不住的惊讶。
“峰子?你一大早跑这儿干嘛?”
徐峰不答,径直走进去,目光掠过四周墙角的文件堆,注意到墙边那个铁皮档案柜上贴着的旧标签已经褪色,只剩一个“”字隐约可辨。
“老周,有点事要问你。”徐峰语气温和,却带着股不容回绝的力量。
“你说呗。”老周不安地站起身,拍拍裤腿。
“八号仓库存的定位器样件,是不是三周前调出过?”
老周眼神微微一顿,随即点了点头:“好像是……当时说是给设备线做次级试装,走的内部转库流程,没走外调审批。”
“批条呢?”
“还在。”他翻了翻桌上的档案本,抽出一张折角的复印单递过来。
徐峰接过来看,眼神一凝。
“申请人:许大茂。”他盯着这行字念了出来。
“这……我也是看着流程批的,他说是你那边的零件组给他授权,让他先走一步紧急借调,过后再补手续。我想着是老熟人了,又不是外调,就批了。”老周擦了擦脖子上的汗。
徐峰冷笑一声:“他什么时候成我那边的授权人了?我都不知道有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