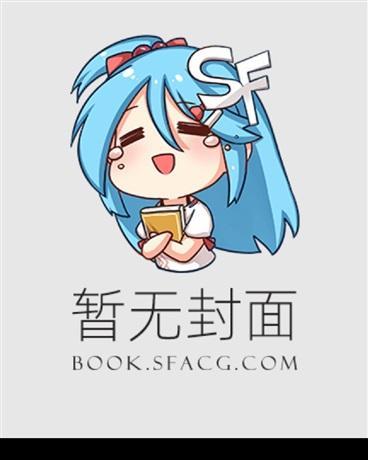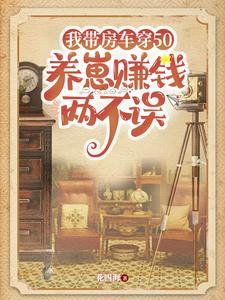青豆小说>被骂上热搜后,顶流赖上我炒CP > 第233章 选择入口(第1页)
第233章 选择入口(第1页)
消毒水的味道无孔不入,像一层冰冷的薄膜,包裹着整个空间。
苏晚的手机屏幕亮如白昼。
陆氏集团买凶刺杀苏晚的标题加粗放大,占据了屏幕最顶端。配图是她躺在急救床上的模糊剪影,被拉伸处理,充满了视觉冲击力。新闻推送的时间,距离她把报告出去,不到十分钟。
效率惊人。
病房门被推开。
轮椅碾过门槛的咯噔声,与她沉稳的心跳达成了某种共振。
陆景行停在病床前。
他膝上放着一个牛皮纸的密封文件袋,指节无声地叩击着粗糙的袋面。他的视线扫过苏晚手机屏幕上的标题,没有停留,也没有任何评价。
像在看一份与己无关的天气预报。
“舆论酵的度,比我想的要快。”他先开口,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
“因为故事足够好。”苏晚关掉屏幕,将手机反扣在床头柜上,“有受害者,有清晰的加害方,还有物证。”
“物证?”陆景行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那份伤情报告。”
“那不是物证。”陆景行说,“那是情绪的催化剂。真正的物证,在这里。”
他抬起手,将膝上的文件袋推到床边。
苏晚没有接。
“匕。”陆景行并不在意她的反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现场遗留的那把匕,编号是k-。”
苏晚的瞳孔微不可察地缩了一下。
一个编号。
不是街边随处可见的管制刀具,而是有特定标识的武器。
这意味着,它有源头,可以被追溯。
“法医数根据库的分析结果,”陆景行的指节停止了敲击,平放在文件袋上,“它与三年前柏林生的一桩悬案里,出现的凶器,是同款。”
柏林。
一个遥远的,与她过往毫无交集的城市。
苏晚的脑中,那条通往自己坟墓的直线,开始出现分岔。这不是程序的延伸,这是一个新的变量。
“所以,陆先生今天来,是来做什么的?”苏晚问,“帮我这个‘受害者’指认凶手?还是替陆家撇清关系?”
“我以为苏导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的帮助。”陆景行的话里听不出任何倾向,“你已经找到了最强大的武器。”
“舆论?”苏晚像是听到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舆论是双刃剑,陆先生比我更懂。它能把我捧上受害者的神坛,也能在我被证明‘撒谎’的那一刻,把我摔得粉身碎骨。”
“你没有撒谎。”
“但我没有证据。”苏晚直视着他,“我只有一份伤情报告,和一句‘陆氏影业,买凶杀人’的指控。这在法庭上,一文不值。”
这才是她计划里最凶险的一环。
她是在赌。
赌对方为了维护陆氏的声誉,不敢真的和她对簿公堂。赌对方会选择在舆论的压力下,用私下的方式“解决”她,从而露出更多的马脚。
这是一场以她自己为诱饵的豪赌。
“现在你有了。”陆景行将文件袋又往前推了寸许,几乎碰到了苏晚的手背,“k-。一个足够分量的证据。”
苏晚依旧没动。
“我不明白。”她说,“陆先生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我只是一个信使。”陆景行回答,“负责传递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事实从来就不是客观的。”苏晚反驳,“选择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人,传递什么样的事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场。”
她的逻辑链在飞运转。
陆景行带来的信息,指向了柏林悬案。这意味着,这把刀,这个凶手,甚至“蝎子”,都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