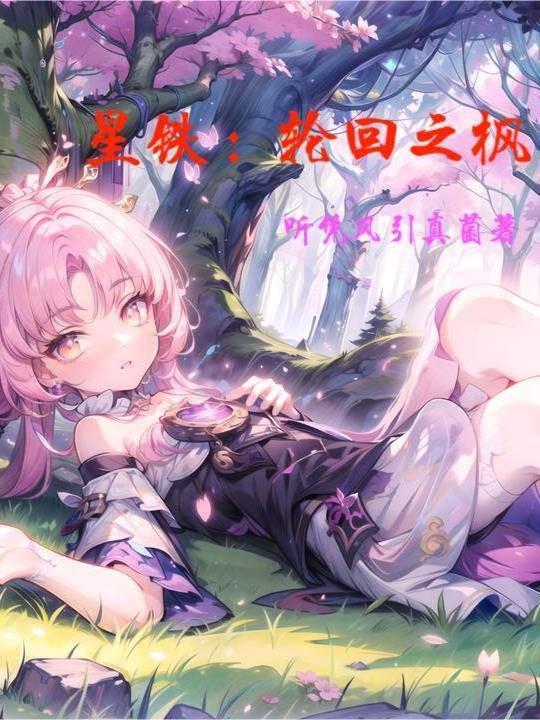青豆小说>1小时相亲,我闪婚豪门 > 第754章 今生她多么幸福(第1页)
第754章 今生她多么幸福(第1页)
“轩逸,我老公讲解的,应该可以打oo分了吧?”
呵呵呵。
阿庭得oo分,不是把冠军拿走了吗?
轩逸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嫂子,成绩待定吧!”
“有秘密!下一个该你了吧?”
诗雅看着轩逸,一脸的欢喜。
多好的兄弟呀。诗雅自内心的喜欢呀。
今生多么幸福,身边围绕着京市的三个大人物。
“好呀,嫂子,你说是我就是我。”
“那你讲唐诗还是宋词呢?”
“唐诗吧,刚刚阿庭讲了唐诗,我也讲唐诗。”
轩逸痛快地回应。
只是究竟讲哪呢?
轩逸思虑片刻后有了答案。
“慕容少爷,你到底要讲哪一呀?快点说。”
林兰催促着。
“就是啊,慕容少爷,急死我了。”
许如兰也补充了一句。
“崔颢的《黄鹤楼》。”
“哇塞,这我太喜欢了,我也能背。”
钟天意兴奋地回答。
“我知道大家都会背,但是大家还得听我讲。”
轩逸开始滔滔不绝。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此诗为崔颢登临武昌黄鹤楼所作,打破七律格律限制,以虚实交错的手法勾连神话、现实与乡愁,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唐诗纪事》载李白见此诗后慨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足见其艺术震撼力。
这诗的意思是说,传说中的仙人早已驾鹤飞离,徒留一座空寂的黄鹤楼伫立于此。黄鹤一去不返,唯有天边的白云千年如旧,兀自飘荡不休。晴空下的汉阳城绿树清晰可辨,鹦鹉洲上芳草如茵,绵延似海。暮色渐深,何处是我的故土?凝望这浩渺烟波,无尽愁绪涌上心头。
昔人:指乘鹤登仙的费祎或子安,事载《齐谐记》。
空悠悠:既状云之飘渺,又暗含时间永恒与人生短暂的对照。
鹦鹉洲:原为武昌江中沙洲,东汉名士祢衡曾在此作《鹦鹉赋》。
乡关:与《诗经·小雅·采薇》“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异曲同工,强化漂泊者永恒的追问。
全诗以“黄鹤”为核心意象,构建三重时间维度。神话时间:联“昔人已乘黄鹤去”引入仙人传说的永恒性,赋予黄鹤楼现实的灵氛。传说与现实的断裂(“空余”)暗示人类对永恒的无力触及。
历史时间:颔联“千载白云”以自然物的恒定反衬人世的短暂,与张若虚“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形成哲学呼应。动词“空”字既写云的自由,亦写诗人的落寞。
个人时间:尾联“日暮乡关”将时间压缩至黄昏时刻,个体的生命焦虑(乡愁)与宏大的历史虚空碰撞,催生出“烟波江上”的终极迷惘。
这种时间层叠手法,使全诗突破传统登临诗的怀古框架,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
诗中的空间布局形成“神话—现实—心灵”三重镜像。垂直神话空间:“乘鹤去”引向上飞升的动势,仙人、黄鹤构成验维度;水平现实空间:颈联“晴川汉阳树”“芳草鹦鹉洲”以工笔勾勒长江两岸地貌,横向展开地理实景的壮阔;纵深心灵空间:尾联“烟波江上”的模糊性消解了前文的清晰视觉,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心理空间。江水、烟雾与愁绪的叠加,构建出中国诗学中典型的“景情互化”模式。
此诗被南宋严羽称为“唐人七律第一”,却有意打破平仄规范,以自由形式强化情感张力。重复的意象暴力:“黄鹤”三度出现(联两次,颔联一次),形成神话与现实的双向解构。重复不仅未显累赘,反而强化了时空错位的眩晕感。
不对仗的颈联:“晴川历历”与“芳草萋萋”似对非对,工整描绘中暗藏流动感。这种半对仗手法既维持了律诗的均衡美,又避免了过度雕琢的匠气。
散文化的结句:“烟波江上使人愁”以口语化收束,冲淡前文的古典意象,让情感以最朴素的方式直击人心,与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异曲同工。
崔颢的乡愁绝非简单的思归之情,而是糅合了多重精神困境。存在的漂泊:仙人已逝、黄鹤不返的意象群,暗喻个体在现代性困境中的无根状态。“日暮”既是实景的时间提示,更是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存在境遇投射。